导语
“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
《论语·季氏篇》 | 儒家提倡的“仁”指的是个人之于社会的责任感,也就是人生的自我价值建立在其社会价值实现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也向知识分子提出“兼济”与“独善”:这则关于进取和后撤的两种处理自我与社会环境之间关系的人生理想。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齐物论》 | 这里指的“天人合一”,即是道家对“真”的追求,中国人抚爱万物,与万物同节奏: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所以根本上是虚灵的时空合一体,是流荡的生动气韵。道家主要的讨论围绕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即对自然建立一种深宏的体恤和敬畏。
以上两种哲学观对文人士大夫在不同时代的影响,得以让“归隐”这条线索贯穿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书法、绘画艺术等文艺经典。通过这些多维的叙述形式在时代的更迭中发展和丰满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生命形态 ,建立了“人与社会”和“人与天 地万物 ”这两个议题在中国艺术中不可撼动之地位。下面两组作品并置了古代和当代的山水作品。通过对比来探讨两个时代中水墨山水的视觉呈现和思想意趣,进而阐释“归隐”这一主题在中国水墨艺术中绵延至今的影响。
“渔人”母题的古今嬗变
中国艺术史的发展中“文人画、士夫画”一直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艺术流派,它所体现的价值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这样的审美价值在继唐宋后的元朝得到了兴起和发展。元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中原的朝代,蒙古族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对汉人采取了残暴的镇压,森严的等级制度和民族归属感的丧失迫使许多文人士大夫在亡国的际遇下隐居不仕、寄情山水。与黄公望、倪瓒、王蒙并称“元四家”之一的吴镇 (1280-1354) 便是其中之一 。

元 吴镇 ,《芦滩钓艇图》 , 水墨纸本卷轴, 31.1 cm × 53.8 cm,ca. 1350 图片来源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品
吴镇,字仲圭,号“梅花道人”,浙江嘉兴人,为一介书生,工诗文和书法,善画山水,为人孤洁,也选择了浪迹江湖的隐居生活。他的山水画中有许多关于渔夫这类隐士母题的作品,这幅《芦滩钓艇图》用简洁苍劲的笔法描绘了一幅渔人鼓棹归家的恬澹情景。在画者浓淡相间的笔触中,迭加或者延展,石礁上蔓延出葱郁丛林的枝叶,似乎随着微风起伏着,随着画者细腻轻松的线条,树荫下的水波缓缓连接起一叶扁舟和渔人,然后视线被指向无尽的天际。即见自跋诗:“红叶村西夕照余,黄芦滩畔月痕初。轻拨棹,且归与,挂起渔竿不钓鱼。梅老戏墨。”
吴镇对画面的处理有着文人诗意的开放布局,笔触之间的过度是秀劲潇洒的,给予观者静谧平远的想象空间。这位置身于和谐自然中的渔人,是吴镇个人情感的理想归宿。表达了文人士大夫远离俗世,在潺潺的水波中,望苍穹的高远,思宇宙的无穷,从而在体会自然的律动中建立起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另一种连接。

艺术家:秋麦 Michael Cherney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秋麦 Michael Cherney,《潇湘八景之渔村落照》,28°47'39" N, 111°25'41” E, 摄影墨本手卷,25.5 cm x 142 cm,2008-2009
沿着时间的线索推进,渔村依旧有叶叶扁舟,情景依旧是夜暮归家,重新叙写这一母题的却不再是画笔,而是相机。700多年之后,时过境迁,但中国历史和审美价值同样形塑着人们对于山水的认知。成长于美国纽约的摄影艺术家秋麦(Michael Cherney)受到中国传统艺术的吸引,从远洋移居到北京进行创作。他广泛游历了中国,在跋涉中不断寻找和中国艺术史有关的古迹和旧址, 透过秋麦的镜头西方的观众得以捕捉到东方文化变迁的脉络,秋麦的作品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亚洲部收藏的当代摄影作品。此《潇湘八景》系列正是纵贯湖南省的潇湘水域的八处佳胜,为宋代沉括《梦溪笔谈—书画》中所描述。它是历代文人墨客山水画创作的母题。秋麦的《潇湘八景》中的八部手卷,遵循了地理上的顺序,作品起始于上游的南部山区再延续至下游的北部湿地;作品中的每部手卷都标记了照片拍摄地的具体地理坐标。同时,每部手卷的标题也与历代的诗歌、绘画中《潇湘八景》的标题一一对应。
《渔村落照》为《潇湘八景》系列的最后一个主题,描绘了渔村傍晚的景象,渔翁满载归家自然和谐的暇意情致;这幅照片拍摄于沅水岸边,正对应着古画和古诗中曾经刻画过的渔村;桃花源的桃花溪也恰恰是在这里汇入沅水。与古代艺术和文学作品中的描绘不同,在秋麦的作品中,挖掘机正在把河床中采集的沙子卸车,顺着机器的传送带将我们的视线延伸到了画面之外。
两幅作品,一古一今,同样是对渔人母题的回溯,秋麦的摄影作品与元朝吴镇画作中对画面的布局设计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具有诗意的开放空间,观者视线得以巧妙地伸展开来,引人思考。不同的是,秋麦摄影的渔村内容显然并非历史中隐逸志趣的视觉再现,两幅作品最终达致的心意也大相径庭;在秋麦镜头中反映了潇湘江流域的环境和本地人生活方式的变迁,和古代《潇湘八景》中的《渔村落照》这个主题形成了对比。对秋麦来说,创作不仅是对过去的回溯,也是对自然的敬畏,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的缅怀。秋麦曾说道:“凝望着一个承载着广大的历史和文化记忆的地方,用摄影来捕捉它的某个瞬间,虽转眼即逝,却也真实存在。”
游走“山水”间的虚实变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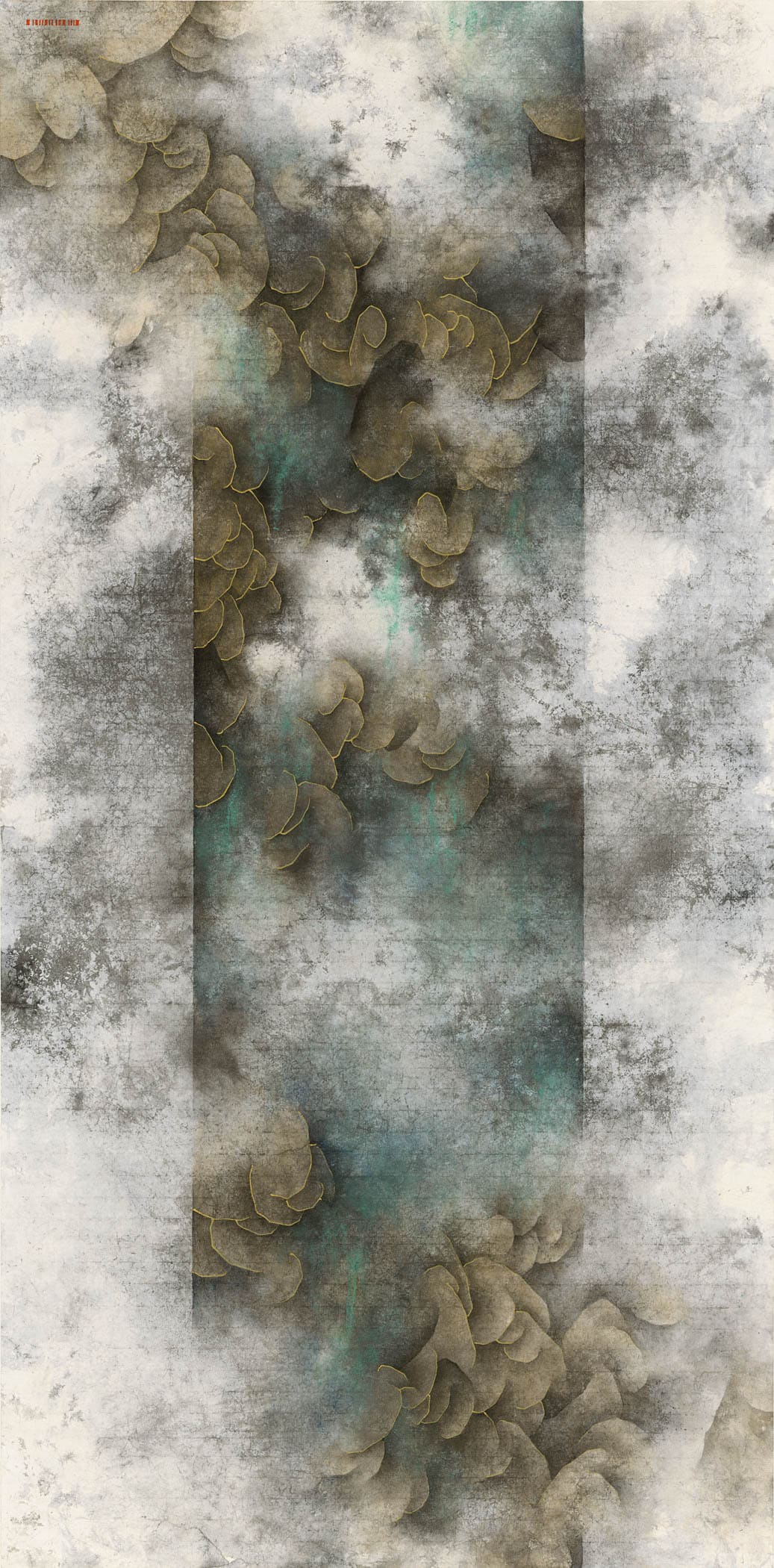
邱荣丰,《蜃境-六》,水墨纸本,137 cm x 69 cm,2019
历史的转折时期,有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艺术作品也会呈现出变革时代中的精神面貌。1644年,中原再次受外族统治,明末清初的遗民艺术家便体现了反正统保守画派的倾向,他们的作品具有革新性和高度的自我表达性。清四僧之一的八大山人(1626年—约1705年)为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明朝的覆灭给当时身为明朝宗室的八大山人的世界观带来了致命的冲击和创伤。失去家国,悲愤的爱国情绪无法改变两朝交替的现实。当时,八大命在旦夕,为逃离清政权的迫害他剃度为僧,隐匿于世,佯疯作哑,一生颠沛流离。个人意志与社会剧变产生强烈冲突,八大封锁了自我和外 界的连接,将内心的积郁和强烈的孤愤内化在了水墨艺术的实践中,创作出反正统保守画派且极具个人色彩的艺术表达,对后世中国艺术流派影响深远。

八大山人(朱耷),《古澹萧寥》绢本,180.3 cm x 49 cm,1864,(王方宇学者旧藏)
《古澹萧寥》是八大晚年创作的作品,整篇格局宏伟高远。山体从底部通过几段平台作为折径直冲云霄,横涂竖抹,笔力强劲,豪迈纵横。虽取自董其昌的笔法来画山水,却绝无秀逸平和,明洁优雅的格调;虽见屋檐错落在苍劲的松林与山石之间,却空无一人,枯索冷寂,满目凄凉。
整幅画面山体顶天立地,给观者强烈的压迫之感,当视线最终被推移到山顶,即见八大自创的奇字画押落款。八大的诗歌、签名、名号都极其生僻艰涩,上世纪的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考据研究才得知其意义。左上方的文字是“个相如吃”,“个”指的是八大山人自己,“相如”指司马相如,史书载司马相如有口吃的毛病。八大的意思是,自己与司马相如一样,都有口吃的毛病。右面是三月十九日,而明崇祯皇帝自缢的时间恰是1644年3月19日。
有别于以“渔樵耕读”这四大隐逸形象为母题的古代山水创作,他的山水画中并未出现这些具有象征性的隐士形象。不过,隐士的特征仍旧可以说贯穿了八大的创作,作品中所书写的文字大多晦涩难懂,这是传达隐逸心境的一种方式。作品右上为近现代大师吴昌硕(1844-1927)题跋,左上角为陆恢(1851-1920)题跋,吴昌硕在题跋中写道此幅作品曾被清画家严恒(严榕斋)的儿子严信厚(1838-1907)藏鉴。可见唯有志同道合之士,才能跨越时空走入他的内心世界。
不同于大部分水墨画家,八大直到晚年才有山水作品存世,这对一位水墨大师来说是极为罕见的。我们推想他或许直至生命的终点才得以与自己和解,开笔创作了雄健简朴的山水绘画。上述这件作品就具有这样的代表性。在《古澹萧寥》中,具有压迫性上升的视觉冲击、荒寂的丘壑、空无人烟的远方以及最后在天际处落款3月19日的这种收笔,是八大为后人留下的暗语:无上崇敬的胸中丘壑已是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家国。
同样是以画山水浇胸中块垒,从八大到邱荣丰,历史语境变迁,虚实手法相类,“归隐” 心境的理解与表达上,形成微妙的互文。

邱荣丰,《驾雾-六》,水墨纸本, 96.5 cm x 179 cm,2019
在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科技发展带来的剧变深刻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山水的认知。人们同样需要山水,也同样憧憬归隐,只是理念和方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邱荣丰1990年生于香港,他的作品曾被洛杉矶郡立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于机构重要展览《吴彬:十面灵璧图》中。他受到卫星图像的构图启发,以片段化的景致创造了“移步换景”的虚拟世界,建构出基于传统水墨审美的一种新的视觉经验。他在《蜃境-六》中将画面空间垂直分割为等比例的三段程式,制造了一种理性机械的隔离感,但絮绕的云雾又贯穿在三个片段之中,这种分割与穿透又共同构成了一种断裂和连续的观感。山石的构图程式和上幅八大的山水类似,同是进退虚实之间山体拔地而起直冲云霄,但邱荣丰的“山”和“水”却化作了极为抽象的视觉符号。
对邱荣丰来说,“抽离”或许是当代最能表达“归隐”的状态。成长于科技形塑的城市之中,科技虽然是基于对真实的发掘和传播,然而其描绘的世界却脱离现实。归隐内心、抽离现实在当下看似显得格格不入,实则是对现代科技所营造的虚拟世界的一 种反应。在资讯爆炸的时代的“归隐”难免需要游走在虚实之间,具有一种忽远又近的矛盾性。《蜃境-六》的中间一段是实景,两边更像是虚焦的景象。画面上的虚实则呼应了艺术家对虚实、抽离、游走的理解。
兼济天下还是独善其身?历代文人尽难两全,如果前者不能得,后者或许是一种缄默的反叛。中国艺术意象中的“归隐”并非纯粹的隔绝,这一后撤的姿态也可以是对身处境况的一种抗争。这种出世的态度并未阻断隐士与外部世界的联系。相反,艺术家、文学家通过回归本真和自然,创造了更为深广的沟通方式。他们以诗歌、绘画、摄影、影像等具有各时代特征的媒介载体,向外部世界传达了内心的声音,寻到志同之人与之共鸣。这种相惜是委婉和细腻的,也更为绵长,在历史的长河中会积聚起更多的意义和重量。





